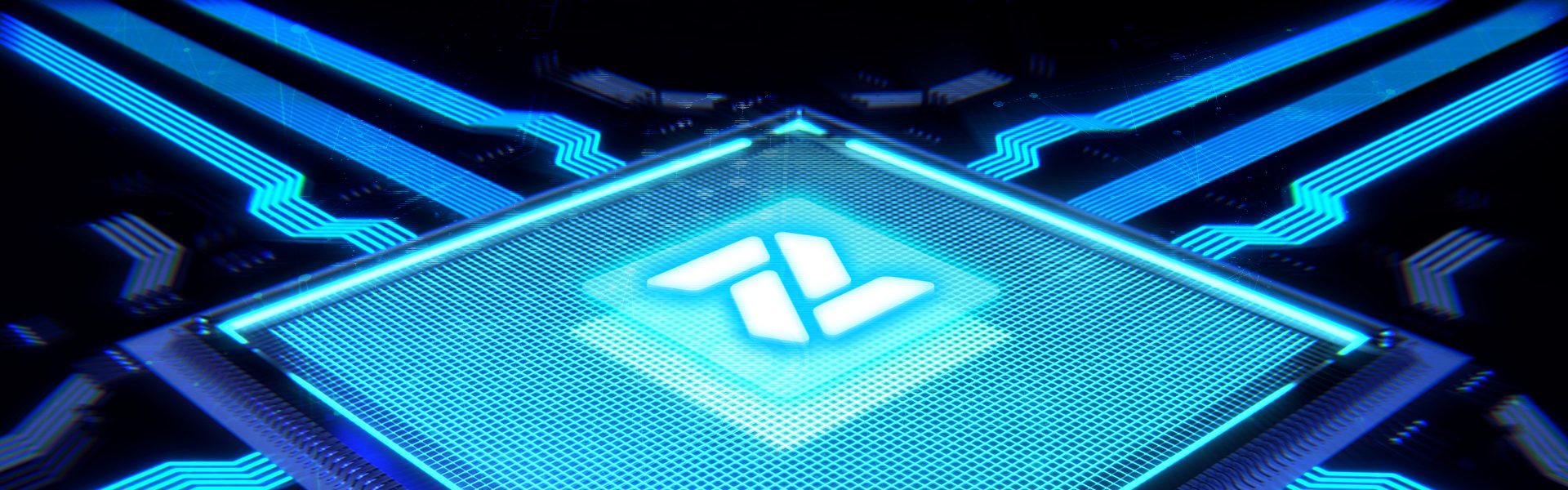數字化大國“補芯”忙,亦別忘了“缺魂”苦

題圖丨視覺中國
迄今為止,在大量或真或假,或夸大或錯誤的網絡信息沖刷下,如今大眾即便不知道半導體是什么,也不會再有一個人對芯片于我國經濟發展究竟有多大的意義提出質疑。
但是,鮮少人愿意對運行在芯片與硬件設備上的基礎軟件投注過多目光。
中國基礎軟件到底有多薄弱,關注開源操作系統的開發者很清楚,大名鼎鼎的Linux操作系統CentOS 社區就在2020年12月發生了巨大變故——廣受開發者好評的CentOS 8 將于 2021 年底被提前終止,今后將只有 CentOS Stream 版本,不再會有 CentOS。太多人不滿之余,紛紛疾呼“CentOS 已死”。
究其原因,有人猜測由于CentOS的核心技術其實來源于美國紅帽公司(RedHat)商業版操作系統RHEL 。紅帽在2014年買下了CentOS,而紅帽公司又在2018年被IBM收購。
而包含了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以及編程語言的基礎軟件產業,很遺憾,在國內雖有生根發芽,卻遲遲不見壯大。與國內不可小覷、甚至風靡國外的應用軟件勢頭相比,它就像另一只晚發育10年的腿。
以操作系統為例,我們熟悉的安卓、蘋果OS及Windows,掌握了全球移動及PC設備的絕對話語權,這才有了時代大幕落下后華為被困、鴻蒙突圍的一系列故事。
而在普通人無法觸及的2B基礎軟件市場,現實則更為骨感。
在這里講個鮮少人知道的小故事:
2020年,一家知名的信息提供商因特殊原因,不得不在6個月內迅速更換一批不受限制的新服務器和操作系統。負責人曾告訴虎嗅,硬件倒好說,最難的其實是要更換系統軟件和應用系統,這里面包括非常核心的大數據、容器云和數據庫。
“當前是基于原有的大數據產品做了很多開發。而在1個月內做大量更換,一個很多系統運行比較久,要做數據遷移麻煩就很多;另一方面,大數據的組件比較多,需要進行軟硬件兼容性適配和重新部署,同時,需要在不中斷業務情況下進行替換,并且性能要高于原系統,技術要求很高。”
沒辦法,他們跟業界IT專家一起日夜梳理出了需要做調整的百余個系統,然后發現,在這種急迫的情況下,必須客戶需求方、操作系統廠商、ISV廠商一起配合做應用層的兼容,才能艱難邁過這個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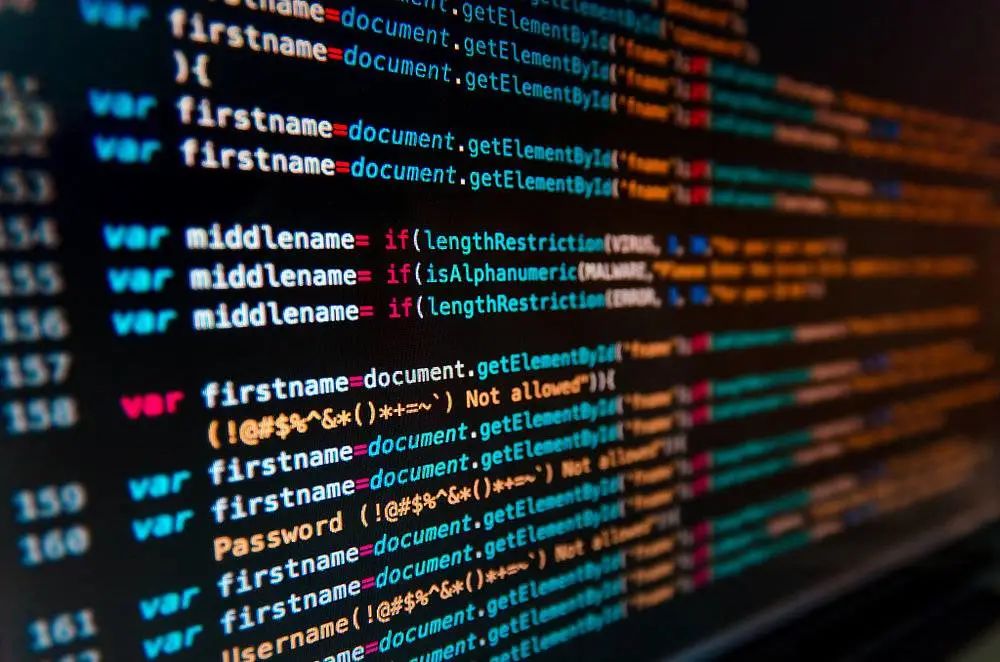
以中間件市場為例,根據CCW Research一份2018年調查報告顯示,IBM 和 Oracle 在這個細分市場的占有率分別為 30.7%和 20.4%,形成寡頭壟斷,幾乎是企業級中間件產品的代名詞。
而他們能在基礎軟件許多品類扼住全球市場命脈的根本原因,無非是體量巨大、產品生態豐富,超過50年的漫長積累,以及相對集中的巨量人才。
譬如,IBM早在20世紀60年代,也就是計算機產業發展初期,企業級硬件產品競爭最為血雨腥風的節點,他們就做出了一個前無古人的大膽決定——在推出一款名為360計算機的同時,歷盡千百種麻煩設計出了配套的系統軟件,并開了軟件兼容的先河。
“IBM做基礎軟件耗費了血本,但卻做了一個延續它后來幾十年IT輝煌的決定。
因為那時候編軟件實在太貴了,而且企業用戶也不愿意輕易更換程序和系統軟件。“好用的軟件還可以敦促企業用戶再換臺同品牌的新計算機,而可兼容的軟件則又可以像傳染病一樣把越來越多的開發者聯系起來。” 《新機器的靈魂》作者Tracy Kidder這樣描述上世紀60~80年代崛起的美國計算機軟件產業。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與世界頂級產品至少20年的時間與速度差距,決定了我們沒有任何空間和底氣說出所謂“彎道超車”這種觀點。而更殘酷的是,由于國內技術標準的缺失,整個基礎軟件產業的絕大數評判標準,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
根據市場分析機構statista提供的數據,截至2019年6月,在全球服務器操作系統市場中,Windows占據了72.8%的市場份額,而Linux與Unix的市占率則分別為13.2% 與 5.4%。
此外,2020年,全球數據庫市場規模為671億美元,而中國數據庫市場規模為35億美元(約241億元人民幣),僅占全球5.2%。
因此,與半導體產業一樣,那塊排布上億只晶體管的硅片之上、應用軟件之下的關鍵銜接處,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位于大眾意識覺醒過程中的“盲區”。
“芯片上肯定要有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以及編程語言,否則芯片根本無法工作。” 一位業內專家告訴虎嗅,業內說的“缺芯少魂”,“魂”指的就是基礎軟件,它在體系里重要性無法比擬。
“而這種東西一旦受到鉗制,對整個行業的影響也很致命。芯片如此,基礎軟件也是如此。” 他指出,2020年,Linux發行版操作系統CentOS開放策略發生重大改變——原來的開放版本已經不再支持正常的商用發布,而這一點無疑會影響國內用戶,需要企業和開發者們尋找替代方案。
如其所說,雖然很多商用軟件產品的“核”都具有開源的特性,譬如Linux,就是一個由荷蘭學生在1991年通過一封郵件開啟的偉大開源系統。此后,平均每3個月,就會出現一款以Linux為核開發出的商用或開放操作系統,而上面所說的CentOS,此前就是開放版本。
也就是說,在特殊的時代條件挾持下,無論開源與否,命運只要一刻掌握在別人手里,就要承擔可預計的后果,而這種滋味,再沒有人比華為等中國硬科技公司更懂了。

然而,即便現在滿天都是“搞芯片、搞工業軟件”的呼喚聲和資本聚攏大勢,但IBM與甲骨文的發展史仍然能給我們最理智的借鑒——單憑一家公司或一個開發者,不可能做出可媲美Oracle和微軟等數百家企業上千種商用產品性能的替代品。
“我們做過一些調查,目前國內真正做基礎操作系統和數據庫的人應該不超過1萬人。” 上述專家說出了這個對比中國14億人口略顯離譜的數字。毫不夸張地說,這個領域的人才珍稀度,堪比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原因就在于,對比應用軟件產業數十、上百萬的軟件工程師,基礎軟件的人才投入實在太少了。” 他指出,由于產業太小,支付不起這么多高水平人員的工資,人才向互聯網的流動趨勢已經變成一種傾泄狀態(這種情況,其實普遍存在于工業領域)。于是,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沒有人干這行;沒有高級人才干,就會導致我們在基礎軟件的關鍵技術無法取得突破;沒法取得突破,就導致基礎軟件的水平低;而水平低了,就越沒人用;越沒人用,整個市場越起不來,就越沒人來。
此外,受歷史文化、產業結構以及教育體系等綜合因素影響,“重硬輕軟”、“重應用輕基礎”,一直是國內工業與IT產業的主流思想。作為一位媒體人,從文字撰寫和表達描述中,其實也能深切感受到,相比硬件的“有形”,無形的軟件知識與學術論點,通常更難被正確輸出給大眾。
當然,對于需要養家糊口、以實現商業成功為目的的軟件開發者來說,軟件知識產權環境與國外的天壤之別,也許是他們最無奈——
“很多公司要靠軟件出海才能賺錢。在國外,假如你搞盜版,可能會被告到狗血淋頭、傾家蕩產;在國內,甚至有做軟件的公司自己用盜版都用的不亦樂乎。”這是一位軟件創業者對我們說出的憤懣感言。
直到2019年,操作系統、軟件生態頻頻被卡,戳到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痛處的 “缺芯少魂”才終于被看見。
我們看到無論是麒麟芯片、鯤鵬芯片、鴻蒙操作系統,還是歐拉操作系統(openEuler),單憑一個華為是遠遠不夠。我們真的需要整個產業以及大眾,哪怕形成一個初步的認識。大家先有意識搞起來,才能把真正重要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壘起來,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慢慢做起來。”
以歐拉操作系統為例。早在2019年,華為把十多年在服務器操作系統領域的積累開源為歐拉。經過近兩年的發展,歐拉社區已吸引6000多名開發者、超過100家企業加入,國內操作系統領軍企業紛紛發布基于歐拉的商用發行版,在政府、運營商、金融、交通等領域規模部署。
不僅如此,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體系,對于缺少基礎軟件開發經驗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2020年,華為曾跟教育部一起啟動了涉及72所高校,未來將擴展到2700所學校的育人項目,也在積極聯合一流學府出版系列教材。不過,這一類人才聯合培育項目,也經常出現在包括人工智能、云計算以及半導體企業的大會宣傳手冊上。

但讓我感到意外的,是2021年4月的一個山東地方技術宣傳活動上,一位最后出場,幾乎無人問津的職業學院校長,稱華為在給他們做一些技工人才成長培育方面的協助工作。
“優秀的工人也缺嘛,我們都是體系里的一環,沒有誰更重要,誰不重要一說。”
我們覺得,有一句在年輕人中非常流行的“名人名言”,特別適合來形容“中國過去沒有,現在仍然骨感,不知道未來是否會好轉但還有人在做”的基礎軟件生態——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